2019年9月,作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孔院新一批中方人员,我们7人满怀憧憬踏上了这座地中海沿线的意大利第三大城市;但怎么也没有料到,6个月后,我们都得以“禁足在家“的方式来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侵袭。

意大利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始于2020年2月下旬——北部的伦巴第大区开始出现聚集性案例,感染者从2位数到3位数再而后到4位数戏剧性地增长,并由北至南逐步“染红”了整个意大利(在疫情地图上,红色代表最严重的地区)。3月初,意大利政府颁布了“禁足令”,自此,我们和所有意大利人民一起开始了居家隔离的日子。
因为有中国的抗疫经验在前,所以我们不像绝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打的是无准备之仗。早在中国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网购了一些口罩,一方面寄往国内,另一方面以备不时之需。有人曾戏说:“这次疫情,中国人打上半场,外国人打下半场,而海外华人打满全场”——确实,国内疫情爆发后,我在这里接触到的每一位华人,无一不是在努力设法为国内提供支援。华商们采购各类抗疫物资发往国内,华文学校的校长们带领师生及家长一面捐款一面以绘画、书法和歌舞等各种形式表达对祖国的支持,在外工作或学习的各类人员也力所能及地参与其中,以绵薄之力抗击疫情,传递爱心。
就拿小小的口罩来说吧。作为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武器装备”,口罩一度成为紧俏商品。各地的华人华侨四处搜集购买口罩支援国内抗疫,加之欧洲各国人民传统理念中“口罩是病人才佩戴的”思想指引,欧洲各国药房口罩的库存本就很少,这些都导致了意大利疫情爆发前后口罩一个难求的状况。这时,小小口罩成为了“巨额财富”,而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无疑也是关爱的流通。

我最初囤积的那些口罩,在意大利疫情爆发之初,使我们孔院的每一位老师和志愿者都有了最基本的防疫装备。但是因为数量有限,面对汹涌的疫情,我们一度非常恐慌。“一次性口罩可以重复利用”,我和老师们强调,唯恐陷入物资匮乏的境地。可就在这时,四面八方的支援来了。学校从非常紧张的物资储备中拨出一部分口罩让孔院工作处给处于疫情中的孔院邮寄,那不勒斯当地华人商会也第一时间从有限的库存中拿出一批口罩分发给当地的留学生和华人教师,我们亲爱的祖国惦记着在海外的游子们——孔子学院总部和外交部联手,通过使领馆给孔院中方人员和留学生们发放的“爱心包”更是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

沐浴着关爱的我们,也努力把这份爱心传递给周围的人们——会意大利语的粟琦老师租住的公寓临街,禁足在家的她就把饼干酸奶等食物装在塑料袋里并配上了意大利语写的暖心卡片,然后用绳子吊在阳台下方供人取用;薛俊杰老师见到她所在公寓的门卫缺少口罩,尽管自己存量也有限,还是拿出了一部分赠送与他。

那不勒斯7家华人社团联合发起了向当地医院捐赠抗疫物资的活动,我虽然没能随他们一起亲力亲为,但是第一时间响应了组织方的号召参与了捐款。


我们做的虽然是点滴小事,但是事实证明,爱心却会因善意而传递。下面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
禁足令颁布后,我们出入办公楼必须有外方人员陪同,虽然没有紧急情况我们尽量避免去办公室,但是一旦有要求,外方院长Paola总是不厌其烦地陪同我们前往。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办公楼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戴着一次性手套,但是嘴部只是用围巾遮挡了一下。
彼时意大利人还在为“究竟哪种方式更能有效抵挡病毒——戴口罩还是注意手部接触”而争论不休,出于好意,我和她说“根据中国的防疫经验,戴口罩和戴手套一样重要”。我原本是想劝说她戴口罩的,没想到,她说,她知道其重要性,可问题是她想尽了办法也买不到口罩。刚好那天我约了老师们给她们送口罩,虽然随身的书包里装的并不多,但是略一思忖,还是匀了一小包(10个左右)给她,她非常激动,连声道谢,说道,“这下好了,我和我的妹妹以及她的孩子都有口罩戴了”,我一听,这么多人这点口罩明显不够,于是另外加了10个给她。
后来在我们得到了各方支援后,我又再次向她赠送了50个一次性外科口罩。她在给孔院总部项目官员的邮件里特地提到了此事,说多亏了中国朋友的帮助,她才获得了这些防疫物资。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给我们孔院担任翻译的华人教师唐女士也缺口罩,就约了给她送一部分,见面后才知道因为国内亲人给她邮寄的包裹一直无法送达,她最初拿到手的几个口罩居然是Paola转送给她的。得知前因后果后,她也不由感慨,正是这些口罩使得我们对彼此的关爱一层层地传递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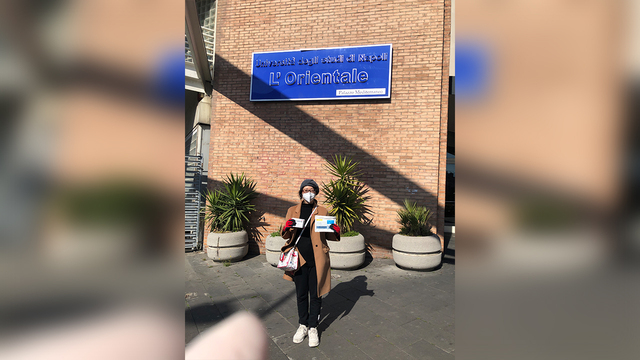
“患难见真情”,小小的口罩串起了一颗颗心,写就了一个大大的“爱”,跨越五湖四海,联结不同族群。病毒无情地隔开了我们的物理距离,但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努力却使我们在危难中拉近了彼此的心。虽然疫情还在继续,但是相信人类只要团结互助,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疫情终将过去,可我们对彼此的关爱将会一直延续。